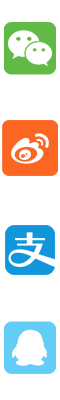綦保国: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的法律经济学比较分析
摘要: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是当今世界财富无偿转移的两种主要制度安排。在西方理论界,关于私人慈善与福利国家的各种理论与思潮相互矛盾、相互制约,争议日久。它们的经济效率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之一。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在经济效率上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但我们完全不应夸大其词,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也同时在经济效率上各具其局限性。从各国的实践经验上来看,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往往并存发展,相辅相成。福利国家不应扼杀私人慈善的自由空间,而私人慈善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福利国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关键词:福利国家;私人慈善;公共物品;贫困保险
中图分类号:D922.18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慈善捐赠人权利研究”(12CFXO27);山东社科规划项目“慈善的事业范围与公益标准研究:基于英美法的考察”(11CFXZ04);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慈善组织高级管理人员义务研究”(12CFXJ03);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山东省社会组织问责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14-ZZ-SH-04)。
作者简介:綦保国(1974年—),男,湖南衡阳人,聊城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信托法、慈善法。
联系方系:手机:18263500601;电子信箱:qibaoguo@lcu.edu.cn。
A Lexeconic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elfare State and Private charity
QI Bao-guo
(SchoolofLaw,LiaochengUniversity, Liaocheing 252059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two main legal systems of wealth gratuitous transfer in today's world, namely: welfare state and private charity. In western theorists , a variety of theories and thoughts on private charity and welfare state mutual conflict, mutual restraint, and dispute with no end .Their economic efficiency is one of the focus.Welfare state and private charity have their reasonable basis on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but we should not completely exaggerated, welfare state and private philanthropic also each with its economical limitati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ountries ,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 and private philanthropy often coexist , complement each other. Welfare state should not stifle freedom of private charity , while private charity can not completely replace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f welfare state .
Key words: welfare state ; private philanthropy; public goods; poverty insurance
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是西方国家财富无偿转移的两种主要模式或制度安排。尽管二战之后,福利国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主导性地位,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的制度缺陷日渐暴露,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的崩溃,新保守主义的观念重新崛起。如果福利国家制度是行不通的,那么减轻或缓解贫困就只有私人慈善一途。在西方许多学者看来,福利国家的“战后共识”的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物质”的,而非“思想”的。[1]换句话说,福利国家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本文将撇开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意识形态的伦理争论,仅就它们的经济效率问题进行剖析。
一、财富转移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财富转移的经济学理由主要是功利主义的整体福利最大化或整体效用最大化。由于财富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将富人的财富转移给穷人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福利。如果假定人们的边际收入效用函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人们对待财富没有乐观或悲观的差异,那么平均分配将能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但问题是人们的边际收入效用函数事实上不可能完全一样,“另一至少也同样合理的假设是,收入和边际效用呈正相关——那些努力赚钱并取得成功的人一般就是那些最看重金钱并为了取得它而放弃了其他(如闲暇)的人”。[2]这样,从一个更偏好金钱的富人转移财富给更偏好休闲的穷人,将可能减少社会总福利。
然而,如果财富转移是自愿的而非强制性的,那么社会总福利将必然增加。这是由于私人慈善的财富转移符合帕累托更优(pareto superior),而任何帕累托更优都会带来福利的增进。帕累托更优的交易是指它至少使世界上的一人境况更好而无一人因此而境况更糟。由于私人慈善具有自愿的性质,那么它就意味着捐赠者并不会因为自己捐赠财富而减少自己的福利即境况更糟。“帕累托效率内含两个价值判断:如果一个人的福利得到了改善,而不会引起其他人情况变坏,这样可以称社会福利得到了改善,而所有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福利的最好评判者。”[3]在诺齐克这样的自由意志论者看来,帕累托更优是获得福利的惟一途径,而私人慈善则是分配正义与经济效率的唯一契合点。“自由意志论者认为最优分配是竞争市场作用于合法所得的捐赠的结果。他们支持通过自愿的慈善行为来救济贫困者——像诺齐克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这是惟一的正当方式——所有的再分配税收手段都具有高压性。”[4]
对私人慈善的自愿主义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搭便车”问题。私人慈善的捐赠者之所以自愿捐赠财富,是因为贫困者的福利与他们的福利彼此依存,这样捐赠者在捐赠财富时不仅贫困者福利增加,而且他们自己的福利也会增加。然而,捐赠者会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帮助减轻贫困。”但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捐赠,这就产生了搭便车问题。其二是私人慈善是不够的,不能达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如果再分配只是富人自愿的,即使没有搭便车的现象,这种制度也不能达到最优。”[5]如前所述,如果平均分配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显然富人不可能自愿将财富与穷人平均分配。
上述分析没有考虑到财富转移的成本。财富转移的社会成本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其一,财富转移本身的成本,例如征税成本。如果是私人慈善,慈善组织也有经营与管理成本。
其二,财富转移对受益者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即培养懒汉。例如失业补贴可能抑制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如果有未成年人的家庭资助这样的社会福利计划就对母亲参加工作有着极大的消极作用。[6]私人慈善也可能培养懒汉,但由于私人慈善具有不确定性,受益者并不能认为从慈善组织接受财富转移是他们的一项社会权利,因此消极影响要低于福利国家政策的财富转移。
其三,强制财富转移必然牵涉到税收问题,而税收却降低了资源使用的效率。政府对一种行为征税,那么必然导致人们转而从事那些征税较轻或无税行为。而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前一行为生产率更高,否则就不必要在征税之后才去从事第二种行为。再如,2001年小布什上台,他提出的一揽子法案题为“经济增长与缓解税收法”,其中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是逐步取消遗产税,原计划逐步递减到2009年全部免去。此案得到大多数共和党议员拥护,赞成者的理由是遗产税挫伤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特别是伤害世代相传的家庭农场主。[7]
总之,如果考虑到财富转移的成本,财富的再分配将不仅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而且必然会减少社会总财富,因此是无效率的。据美国学者估计,“当我们计入所有的财富转移社会成本时,政府每进行1美元的转移,就会有23美分的流失。”[8]当然,从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私人慈善的财富转移成本明显要低于政府福利计划的成本。
二、公共物品理论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福利国家和私人慈善为社会大众提供大量的非现金福利,如教育、国防、治安、医疗、公园、道路、桥梁等,所有这些它们在学术上通常称为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由福利国家和慈善组织采用非市场方式生产和提供,而且它并非是直接针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它的受益对象是一定范围的全体公民。因此,它对不同收入阶层的财富分配影响十分微妙,这主要考虑到分配资源的来源及受益群体的不同情形。由于福利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其成本主要来自强制性征税,那么税收主要是由穷人负担还是由富人负担就变得十分重要。在我国,针对富人的财产税少之又少,事实上穷人支付的税收一点不比富人少,当然主要是间接的价格税。即使是在存在大量财产税(如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等)的西方国家,“穷人支付的税收虽然要比人们想象中的多,但其在财富转移中所取得的比其支付的税收还多,但也许只是多了一点点”。[9] 公共物品的主要经济学分析的焦点是为何要采用非市场方式组织生产和消费,由政府和慈善团体采用非市场方式使用资源是否有效率?
(一)市场失灵及合约失灵理论
一般来说,通过自由市场来分配资源是最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因为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让资源利用最有效率。但是,市场并非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最有效率的,它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也被称之为有效市场假设,包括完全竞争、完全市场、完全信息及不存在市场失灵。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有效市场条件都必须严格具备,而事实上,完全达到市场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完全信息”为例,如果消费者要获得完全的信息,往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其结果同样是无效率的。还有,也并非有效市场假设不完全成立,就必然要采取非市场方式组织生产,政府可以采取一定措施弥补市场的不足,如管制或财政补贴等,这些措施并不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生产的有效性。
然而,有一类产品被称之为“纯公共物品”,如果由市场来生产则注定是低效的。纯公共物品在技术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10]“一旦公共物品被生产出来,非排他性就导致不能阻止人们对这一产品的使用,因此也就不可能进行收费(这就是“搭便车”问题);这种情况下,市场将完全失灵。非竞争性指额外用户的边际成本为零(虽然没有额外单位的产品)。因此,有效价格应该依据个人对商品的边际定价——也就是完全价格歧视。不以此为据,那么市场很可能是低效的。如果要想充分地提供公共物品,那么适当的干预形式一般就是公共生产。”[11]
另外,对于非纯公共物品采用非市场方式生产,如医疗服务并不具有纯公共物品的两个特性,其经济学理论根据来自于合约失灵理论。1980年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在《耶鲁法学杂志》上发表了《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合约失灵理论。“亨利·汉斯曼认为,由于营利性组织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接受其产品和服务时,往往缺少足够的信息来评估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就很可能利用自己在信息不对称关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以次充优、以小充多,欺骗消费者,以谋求自己利润的最大化。”[12]这一信息不完全的情形在医疗服务领域体现得特别明显。
(二)公共选择和政府失灵理论
由政府来组织公共生产是否有效率呢?对政府公共生产的解释有四种理论:其一是市场失灵;其二是公平分配;其三是选民强制;其四是官僚自利。政府失灵理论主要是指后两者,它告诉我们政府行为并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利益集团或者官僚个人及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政府行为并不比市场行为完美,其缺陷可能更大。
选民强制的再分配理论最早见于美国学者唐斯(Downs)的论述。“唐斯认为政治家们为了收入、地位、权力等原因谋取政治地位,因此他们会选择一些政策,这些政策能够使他们在下一届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尽可能地最多;市民们给能够带给他们最高预期效用的党派投票。因为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是,数量相对很少的一部分人取得高收入,而绝大部分人的收入则很低。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对富人财富的更新分配,而从收入较低者那里获得更多的选票。”[13]塔洛克(Tullock)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选民团不仅由最穷人组成,而且更多的中等收入阶层也在其中。他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对穷人的公共支出常常低于对中等收入阶层的支出。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也赞同塔洛克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倾向于反映中位选民的偏好。这样做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对公共物品的过度需求,另一部分人的特殊需求却得不到满足。[14]加拿大学者R•Mishra也认为,“尽管新保守主义者在原则上反对普遍性而主张选择性的方法,但在实践中他们一直未能收缩诸如医疗保障、养老金和教育等普遍公益。主要原因看来是大众对这些普遍公益具有广泛而持续的支持。由于普遍公益被所有人或薪水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选民对它们的支持是全国性的。因此毫不奇怪,在‘对普遍社会服务实行收缩或私有化’的直接建议面前,里根和擞切尔政府都后退了。”[15] 这种选民强制的结果是保守主义政府对贫困者的支持和开支减少,但对中产阶级有利的普遍公益支出却持续增长。概而言之,选民影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动作,强制投票箱与利益集团的游说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政府失灵。
另外一种颇具影响的政府失灵理论来自布坎南(Buchanan)和托里森(Tollison)的公共选择理论,塔洛克(Tullock)也参与其中。布坎南和托里森在其合著的《公共选择理论》一书中指出:“一切传统的模式都把经济决策视为制度的内在变化,而把政治决策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和生产进行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却是将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模式,该模式注意到:承担政治决策之结果的人就是选择决策人的人。”[16]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代表的这种理想化认识与现实相距甚远,行使经济选择权的人并非“经济阉人”。我们没有理由将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神造物。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会犯错误,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自身的私利。布坎南在其与塔洛克合著的书中指出,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17]
公共选择论者认为,如果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那么政府行为也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政府主导的公共生产也可能会使资源使用的效率低下,这就是政府失灵,其原因是:(1)缺乏竞争。使社会支付的服务费用超过了社会本应支付的成本;(2)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不计成本地向社会提供不恰当的服务,造成浪费;(3)政府官员的确是不能为所欲为,他必须服从当选者和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然而,由于个体和集体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使实行监督的效果显得非常有限。政府代表的态度一般都更倾向于捍卫被监督部门和利益,而不是捍卫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利益。[18]因此,政府干预或政府生产并不是永远的最佳办法。
(三)第三部门供给与志愿失灵理论
如果说市场失灵为政府提供的必要性作出了有力的经济学解释,那么公共选择理论却告诉我们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也会存在双边垄断、信息不对称以及预算最大化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公共物品需求的种类、层次、数量会发生不断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在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体现在需求的数量会不断增长。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刚性特征,在类型上具有单一性,在层次上具有全国性或区域性,在效果上具有强制性。因此很难适应人们对于公共物品不同种类、层次和数量的需求。[19]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第三部门供给理论应运而生。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导致了第三部门供给理论的快速兴起,第三部门具有的灵活性、低成本性、非营利性、志愿性以及资金来源的多样性等方面的特点的确也造就了它在效率方面的诸多优势。然而,第三部门,包括私人慈善组织,提供社会公共物品是否真的有效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考验。
首先,与政府提供一样,作为一种非市场产出,其绩效存在度量方面的严重困难。“个人物品的计量、计价和分装出售是相对容易的,而公共物品的处理远非如此简单。……通常很难——并非不可能——界定和测量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的绩效。”[20]美国学者查尔斯·沃尔夫指出,很难按原则去规定非市场的产出,实践上总是产生错误的规定,而且很难进行定量的度量和定性的评价。[21]事实上,人们往往“把那些看不见的收益和成本纳入到组织绩效,如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和非营利组织的慈善形象和声誉纳入到本质上对非营利组织极小的客观度量”。[22]
其次,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慈善组织产权的特殊性,最终导致慈善组织本身及其管理者既缺乏资本市场的约束,也缺乏有效市场竞争的激励。“一项可从其原始捐赠基金获取大量永久性收入的慈善基金是一种不在任何产品市场或资本市场上进行竞争、又不拥有任何股东的机构。基金的受托委员会是一种自我永久性的组织,除了它自身外,它不对任何其他人承担基金事业业绩的责任。同时,由于受托人和其职员都不拥有对基金资产或收入的财产权,所以他们就不可能积极地使基金资产或收入的价值最大化。在此,胡萝卜和大棒都不起任何作用。”[23]波斯纳在此虽是以慈善信托举例,然法人慈善组织一并如此,并无差别。
再次,“公益人”假设的理想与“经济人”理性假设的现实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人们总是假定“公益人”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从比较优势来看,纯公益人提供公共物品不仅成本较小,而且经济效率较高——如果将私益人之下的帕累托最优比作是世界上最高的‘珠峰’的话,那么公益人假设可以产生‘超珠峰’,它的高度可以是——打个容易理解的比方——8848米再加上1000米。”[24]然而,整个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之上,而现实也突显了这一点。“公益性社会组织领域那些血淋淋的现实就是制度型公益性社会组织人性复杂性和变异性的最为有力的佐证。”[25]慈善组织管理者的贪婪与丑闻不胜枚举。
最终的结论就是志愿也可能失灵。正如世界银行出版的《非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原则》一书所强调的,“慈善团体并非必然是好的,相反,它们常是无效率的、非专业化的,即存在着所谓的‘志愿失灵’的问题,有些非营利组织甚至有贪污舞弊的行为。”[26]
三、贫困保险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贫困的原因之一是坏的运气或各种偶然性因素,如疾病、灾害、车祸、失业等不确定的不幸事件。因此,贫困救济的另一经济学理由是以厌恶风险为根据的。如果人们是厌恶风险的,那么人们愿意为其未来某种不幸的可能性进行保险。贫困保险可以防止人们在一些情况下变得穷困潦倒,给人们编织一张经济保障的“安全网”。
贫困保险可以由私人提供,这就是商业保险。然而,商业保险市场的存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必须有正的需求。也就是说,保险只适应于厌恶风险的理性消费者。如果人们对风险不是厌恶的,是中性的或者喜好风险,那么保险将没有市场。从事赌博活动就是人们喜好风险的一个例子。
其二,必须有以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提供保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人的风险厌恶能充分弥补保险人的管理成本和正常利润,才能以一种可接受的价格提供保险。
其三,有提供保险的技术上的可能性。这里主要涉及保险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
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都是关于福利国家效率争论的中心问题,下面我们将分别予以讨论:
(一)道德风险
如果可以通过购买火灾保险防止火灾损失,那么投保人就可能减少购买消防设备或减少其它预防火灾出现的成本。如果有可能通过保险而防止贫困,那么购买保险的人的工作和节俭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而从事高风险的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就会上升。这就是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会导致低效率,例如引起可以防范的火灾,或抑制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最严格地讲,没有道德风险的条件要求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与投保损失都应该是外生于个人的。也就是说投保人的个人行为不能影响到事件发生的概率和事件造成的损失。稍宽松一点儿讲,只要个人影响概率或损失的成本大于从中得到的收益,道德风险就可以规避。
就道德风险来说,商业保险与政府强制的社会保险处在相同的位置。政府强制的失业保险与商业保险一样,可能导致人们不去竭力寻找工作;政府强制的医疗保险也与商业保险一样,可能导致医疗成本的上升。如果医疗成本不受患者的支付能力的限制,人们就会倾向于过度医疗。有人干脆把老人送到医院,就不出院。对患者或医生来说,反证医疗成本由保险负担,他们都将获益。为了改变道德风险的发生率,政府或私人保险公司可能会为贫困保险设定这样或那样的条件。因为政府拥有私人保险所不具备的权力,所以政府可能更好地控制道德风险。“也许最重要的是,‘依福利生存’所带来的耻辱,而这是你购买保险单而取得收益所不可能产生的。这种耻辱感可以减少社会保险道德危机的发生。”[27]
(二)逆向选择
所谓逆向选择,就是指风险概率大的人更愿意投保,而风险概率小的人却不愿意投保。对保险公司来说,保险公司企图吸收良性风险人和回避恶性风险人,这种做法称之为“撇取奶油”。人们贫困化的可能性差异极大。那些可能贫困化的人就可能大量购买贫困保险,从而使保险费率上升而对不太可能贫困化的人不具吸引力,这又将使保险费率上升,而且很有可能最需要这种保险的人无力支付费率。如果被保险人的总人数下降到了只包括那些在近期非常有可能贫困化的人,那么这种结果就是肯定的了。社会保险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它不允许任何人退出保险。因此,政府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在规避逆向选择上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
私人慈善也具有贫困保险的功能,但显然它的不确定性导致其这一功能极其微弱。也就是说私人慈善不可能提供足够的保险。“捐赠人无法保障在其成为穷人时从私人慈善业处得到任何使其效用最大化所必需的资助。”[28]因为向私人慈善业捐款的富人对穷人福利的估价比穷人对其自己福利的估价要低得多,所以人们在进行捐赠时,很少会认为自己在进行某种形式的投保。但组织免费献血的慈善机构,如果承诺献血者在未来有受血需要时享有优先权,那么还是可以更多地激励一些人免费献血。
综而言之,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在经济效率上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但我们完全不应夸大其词,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也同时各具其局限性。从各国的实践经验上来看,福利国家与私人慈善往往并存发展,相辅相成。福利国家不应扼杀私人慈善的自由空间,而私人慈善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福利国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一切福利事业都由政府包办和控制的局面应该且必须改变,给予私人慈善合理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学者比较一致的呼声。
[1] [加]R•Mishra:《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页。
[3] [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穆怀中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4] [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穆怀中等译,第95—96页。
[5] [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穆怀中等译,第92页。
[6]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第606页。
[7] 参见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8]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第606页。
[9]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第598页。
[10] 参见杨道波:《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71页。
[11] [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穆怀中等译,第85页。
[12] 杨道波:《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第74页。
[13] [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穆怀中等译,第90页。
[14] 杨道波:《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第72页。
[15] [加]R•Mishra:《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6] Buchanan, J.M. and Tollison, R.: Theory of Public Choice: Political Application of Economics,MihiganUniversityPress, 1972, P.68.
[17] Buchanan, J.M. and Tullock,G.:The Calculus of Consent,MihiganUniversityPress, 1962, P.5.
[18] 参见[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文版译者序言》,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19] 杨道波:《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第72页。
[20] [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司部门的伙伴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21] [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22] 杨道波:《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第76页。
[23]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第666页。
[24] 杨道波:《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第81页。
[25] 杨道波:《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第82页。
[26] 转引自虞维华:《从“志愿失灵”到危机:萨拉蒙非营利组织研究疏议》,《行政论坛》,2006年第2期,第92页。
[27]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第607页。
[28]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第607页。
原载《聊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 2024-05-24
- 2024-05-24
- 2022-10-06
- 2022-10-06
- 2021-12-21